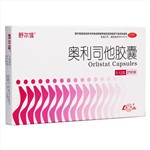一种医学的诊疗方法进入中小学课本,你见过吗?目前,中医药基础知识、针法、灸法、推拿、食物保健等中医养生保健手法走进了我国中学生的课堂。
中医药学是我国的国粹,其中针法、灸法、推拿、食物保健等养生保健方法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宝,但现实中有很多人,对中医一知半解,甚至迷信西医,反对中医,并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
但在“坚守中医”这条路上,有些人从未停止过脚步。
谨以此篇感念颜德馨先生的文章,与所有用全部的信念和生命去相信中医、推广中医药的人共勉!!
时若论
名医,脑海中必现从容正坐一老者,伏案搭脉,望面望舌,静听病患之所苦。霎时目中一亮,神态愉悦,口中默默念出:《内经》有云如何如何,仲景治之如何如何,笔下即出本草一味味,垒而成方。待来日病患复诊,幸喜之情露于言表,于是众坐抄方者皆以惊叹投之。不知一方背后有着多少岁月背诵经典的辛劳,多少日夜孜孜以求,前后参文的执著。然功夫一到,加之临证日久,悟从心生,名医之途正也。
这是已故国医大师王绵之(1923-2009)的一段文字。我很着迷于这段文字,因为它雕刻了一代中医的群像,里面有那群人的神韵,满足了我们对他们的想象:高超医术、仙风道骨、怡然自得……充满出世的智慧、入世的慈悲。
而我看到的是这样一位老人:欢乐苦短,愁苦实多,为人治病疗疾的愉悦只是他人生硬币的一面。
“我这一辈子什么都没有,白白度过了。但是我就是觉得,中医和京剧一样,我之所以做这么多事情,就是想这样一门有用的科学,咱们中国人自己几千年摸索出来的东西,不能弄丢了。
中医不是空的。
中医不是空的。”
中医已成为他的生命。
1920年,罗素在中国客居一年后写成《中国问题》这本书。他看见外来的影响使得中国文化正在发生急遽的变化,中国可以如何应对?罗素提出建议: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
但是随后的中国走上了一条与传统毅然决然分离的道路。
这生生斩断自身传统的痛让王国维自沉、陈寅恪自隐。同样使中医落入了救亡图存的百年迷局中。
而这百年是科学与实证的时代。即使1930年的英国诗人艾略特吟唱着“我不再希望重新体验,那实证时代摇晃的光芒”(《灰色星期三》),科学主义还是以它璀璨的光亮横扫整个20世纪,把它的影子遍布整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作为“科学”的对立面,与“落后”生产方式(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行医模式,中医的命运无疑是悲惨的。
1927年,王国维自沉之初,陈寅恪撰挽词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盛……”这也是属于一代中医人人生的最准确阐释。
每个人都属于一个时代。如果一个人跟上时代主旋律,乘势前进,这样人生顺利的几率会高很多,所谓时势造英雄。但是,有一些人,偏偏被安排在命运的角轮上,在命悬一线即将被时代巨轮旋出去的时刻,反向行之,逆流而上。
怀疑、质疑、蔑视、边缘化、畸化、被提议废止、禁止或者“被保护”……是他们生存的阳光、空气和水。
如果不设身处地,我们很难想象他们的生存环境:妥协、隐忍、心灰意冷、自欺欺人、改弦易辙……如果
不够自信,基本就会放弃;如果不足够强大,基本上就要被他灭或者自灭。
颜德馨先生正是这个群体的一个代表:从他一出生,就别无选择做中医,从他选择做中医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这个行业整体性的不可逆转的衰落。
他自强。内练苦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自创衡法,终成一派。
他包容。他行中医,也不排斥西医。他要的,是真正的中西医并重;他读辛稼轩词,临三希堂法帖,也穿西装打领带;他是京剧票友也爱好西方电影;在孙辈的记忆中,他带他们旅游,还喜欢说两句英语,自名为“90后”,乐于尝试各种新鲜事物。
他积极入世,有言又有行。
大病重病冲在第一线,提倡
中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化、以个人名义成立基金会、创办大师班、为创办一所原汁原味中医院殚精竭虑……
他的晚年,已经桂冠加冕,却仍敢于刺破华丽的外表,说出真相,还身体力行,去做,一点点做。
一个人的一辈子,一直处于一种与时代大势相逆的位置上。一生的规定动作是:逆流而上。当然他可以选择转身、弯腰,选择偏离方向躲避最强大的气流,甚至选择逃跑……然而他没有。
他一辈子都在坚守阵地,把疾病当做战场,攻坚战、阵地战、游击战……
他说:只要你相信你能治好一种病,你就一定能治好它。
犹如以身挽水,逝水如斯,如果挽水的衣袖排成成行的树林,甚至能隐约看见水中垒起的山峰,那将是多么波澜壮阔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