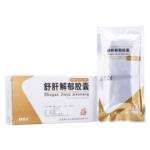“我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是父母的负累。
2017年4月,阿斐走进我的咨询室,一袭红色风衣,上面绣的是白色的仙鹤,轻快的步伐,明媚的笑容加上180的身高让人无法想象那些她曾经告诉我的生命故事。
这一次稍微有些不同的是,阿斐不再是我的来访者,而是我的访谈对象。
5岁那年,阿斐的父母离异了,但有件事情对她影响至深。
事情是这样的,父母离异之后,有一天原本是父亲要来接阿斐离开幼儿园的。可是阿斐从4点多等到了6点,父亲仍旧没有出现,于是阿斐打电话给妈妈说:“妈,爸不要我了。”当时她想表达的意思,可能只是爸爸没有来接她。
妈妈接到电话后火速赶到幼儿园,恰好爸爸也在那个时候到了,两个人便因为阿斐的这句话在幼儿园门口大打出手。
阿斐从那个时候就觉得是自己亏欠了父母,她对自己说:
“你是他们的负累。”
于是,在上高中之前,她生活的主线故事,就变成了“怎样不成为父母的负累。”
阿斐的父亲在他4岁的时候被人打了,加上本来身体就不好,当时医生说他活不过3年。父亲总给阿斐一种胸怀大志,却身陷囹圄的感觉。
从小特别懂事,希望自己“不成为父母负累”的阿斐,也总觉得父亲需要她的支持。于是在大四毕业的那年,原本在北京上大学的她,选择了回到家乡工作。
她以为回家以后,可以“拯救”父亲的生活,做一个主流宣导的孝顺女儿,从此父女情深,家庭和美。然而一年半的现实告诉她,再婚多年,父亲的生活其实早已与她无关。
但阿斐跟我说她还是很庆幸自己回去了,因为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好,那一年半的陪伴仍旧对她来说是重要的。
发现自己待在家乡的意义已经不大了,阿斐在一周里离开了家乡的公司,只身来到北京。来到北京之后,最开始她干起了电话销售的工作。
并不擅长的她,在这份工作中充满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随后她选择了辞职,这段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时间里,她觉得自己越来越低落。
之后在一个老乡姐姐的介绍下,她去了一个基金公司做互联网行业的行研。那个时候她的月薪只有2800块钱,每天上班的时候她都很焦虑,下班的地铁上阅读的时候效率却异常地高。
后来公司派她去武汉出差,她头脑中那些自我否定的声音更加强烈了,工作似乎并没有实质性内容,她没有项目做,感觉自己每天都在混吃等死。
这个时候每天萦绕在她脑海中的,是跳进附近的东湖,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不得不日日面对自己的质疑:
“我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阿斐告诉我,这个时期对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海灵格的《这一生为何而来》。作为家庭系统排列理论的鼻祖,海灵格的书让阿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有渊源的,也是很多机缘契合的产物。
在家族长长的脉络里,此刻的她,只是时间洪流上的一个横断面,大部分都是由历史渊源所决定的现状,而非自己的存在所导致的。
她开始不再那么责怪自己,不再鞭打自己,不再相信是自己害了父母,而是开始正视家庭本来的样子。
那个清明节她一个人去了武当山的寺庙,虽然没有提前做任何准备,一切却顺利到不可思议:她的住宿,吃饭还有行程几乎有如神助一般都一一解决了。因为她精神低迷,她的好朋友也在那个时候赶到了武汉陪她。
阿斐说,她觉得自己是幸运之人,突然间觉得她会变得更好,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帮她。
阿斐告诉我,阅读海灵格的书和心经,对她来说是自我慈悲的开始。海灵格在书中一段冥想指导语中写道:
“我童年所发生的坎坷并非我自省决定的命运。这个坎坷遭遇或许让我无力招架,沉重不已,但我依然尊重这份坎坷命运。比如被送人领养或是生父不详等,我接受并认同我的命运如是,我也因此赢得一份特别的力量。然后我充满敬爱看着我的父母,我告诉我的父母:‘我的生命源自你们的精血,或许这让我因此于罪过联结,即便如此,但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接受认同我的命运。’”
这一生为何而来,在历史脉络里看到自己的家庭,看到家族的脉络,敬畏生命并接受命运,阿斐说这是她学到的第一门功课。
“抑郁,是我所习得的最大的力量。”
——我拯救了自己的生命
2016年11月阿斐第一次来找我做咨询。
就在找我咨询的前一周,她告诉我她试图用上吊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然,这不是她第一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第一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发生在大学。阿斐从高中开始喜欢一个男孩,当我问到他吸引她的地方是什么时,阿斐可爱的说:“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还可以跟人这么交流,他可以理解我。”
阿斐用爱浇灌着这段友谊,甚至在他们上了大学之后,有一次男孩跟阿斐说有女生向他表白时,阿斐拖着当时受伤的腿,跑到男孩的寝室里跟他的室友们商议如何让男孩跟那个女生在一起。这个女孩如今已经是男孩的妻子了。
我问阿斐,为什么要帮自己喜欢的男孩追求别的女孩子,阿斐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不用照顾自己的感受,我可以把自己当作空气,只要在他身边就好了。
就像小的时候我可以把自己当作空气,让自己去照顾父母的感受一样。”
但当男孩和女孩真正在一起的时候,她才开始感受到难以忍受的心痛,也是在这个时候她想过走上宿舍的楼顶上,结束自己的生命。
碰巧的是,当她真的站在楼顶上这么想的时候,关心她的室友发现异状,看护、陪伴她走过不易。
就像后来在武汉想要跳东湖却有力量让自己去武当山寻求答案的她一样,这次阿斐选择了去另外一座城市的大学里当交换生。
在当交换生的这半年里,她似乎又找到了一些活下去的力量:她发现不仅学校的课业她完成的不错,跟同学关系很好,甚至她还在某个课堂项目里带领了一只小团队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成果展示。
然而抑郁后来还是会时不时找她,她来找我做咨询,就是因为常常想结束生命。
我们的咨询真正开始有突破时,其实是在一次危机干预的电话里。
夜里11点40,我刚好准备睡觉,意外发现阿斐给我来的短信,短信里说她已经写好了遗书还有给所有人的信,她害怕自己随时会结束生命,好朋友建议她向我求助,于是她发短信给我。我无比庆幸那一天我临睡前看了手机。于是,我打给了她。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问了怎样的问题,但阿斐告诉我,我的问题让她第一次意识到,她脑中的那些个被她称作是“理智者”,“调停者”,“小女孩”还有凶残的“杀人者”,其实都不是她自己。
她告诉我从前她觉得自己需要去理解和包容她们,但现在她终于明白“宽容不等于忍让”,她要夺回用她的话说,自己生命的主盘。
就像她在从前无数次地拯救了自己的生命一样,这一次她选择不再听从脑中这些声音的想法,不再一味理解和让渡,而是夺回自己生命的主权。
那次的对话是一个转折点。
之后,她开始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在下次咨询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告诉我,现在她想做的事情,就是全心全意地来“讨好自己”。
于是除了我们的咨询,她离开了原来所在的行业和工作,在2017年新年去南方某个著名的寺院里禅修了10天。
在2017年4月我们的几次访谈中,我问阿斐,曾经的抑郁给了她什么。
阿斐说到,从小因为觉得是自己导致了父母关系的破裂,所以她从小就学会了别人的眼光(父母)看世界,并且从小就有很强的观察和自省能力。
但这些东西同时是洪大的信息流,有时候会让她不堪重负,让她忘记了自己。
不管是忘记了跟身体上的自己连接,还是跟心灵上的自己连接。
她说抑郁对她来说是一个邀请:
邀请她去“讨好自己”,邀请她重新理解过往并不再贬损自己,
邀请她去看到她不是她脑中那些个声音,她可以夺回自己生命的“主盘”,
邀请她去学习自我观照和自我慈悲的艺术,邀请她去看到,她可以不用那么努力。
前两天参加台湾后现代心理学家吴熙琄的叙事工作坊,她在跟一个称自己是“焦虑症”患者的人对话时,说了下面的一番话:
“焦虑是宝贵的资源,它需要被听见,被理解。我们不能歧视焦虑。我们来好奇焦虑的盼望是什么?它可能有它的用心。我们珍惜焦虑的盼望,问问它:’你希望我做些什么?’”
在跟阿斐的咨询和访谈中,我学习到抑郁也是如此。
我们同样不要歧视抑郁,如果我们一直不照顾自己的感受,不聆听自己,不尊重来自自己的声音和渴望,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是空气去不断满足别人的需要,那么抑郁是来提醒我们开始自我慈悲和自我观照的旅程的。
抑郁也有它的盼望,它希望被我们看到,希望我们尊敬和欣赏自己生命的全部状态,停止我们的自我苛责。
对,抑郁是我们的好朋友,它只有在邀请我们进入另一种跟此刻不同的生命状态时才会出现,只有在邀请我们转变和整合生命时才会出现。
阿斐说:“抑郁,它对我而言不是一个病症了,它也不是是否能治好的问题,我不再惧怕它的出现。这是我所习得最大的力量。”
看到生命本来的样子,让我变得强大
——我以此回应死亡叩问的答卷
阿斐在我们开始咨询时便告诉我一件对她现在27岁这个年纪来说有些沉重的事情。
2015年6月,当时还只有25岁的她,在很多次被不同的医院误诊之后,终于被医生告知,得了甲状腺癌。
阿斐说那是她人生特别黑暗的一段时间。
她还记得就在她手术期间,爸爸和后妈过来照顾她,但后妈却因为跟她有些意见不和就离家出走,而爸爸选择站在后妈的那一边。
因为医生说做完手术她需要回家静养,所以她就跟着妈妈准备坐飞机回家乡,妈妈自己的身份证在机场不见了,对着无辜的她在机场里人们的众目睽睽下骂了40分钟。
她说那一刻,她对父母的期待都破灭了。
她似乎一瞬间就让自己冷静下来了,看着那个骂她的妈妈,她对自己说:“她骂的不是我。”
从小阿斐就有一种觉得自己活不长的想法,我问她这个想法是哪里来的,她说可能是觉得自己从小就思虑过度,担心自己会殚精竭虑。
但是当死亡的议题真的真的摆在她面前时,阿斐说,死亡和她想象的不同。
曾经她觉得死亡可能是一种她长期压抑自己感受的“报应”,甚至她也想过“我为什么得病?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这样的问题。
但是现在她告诉我,死亡是善意的提醒,提醒她关注自己,提醒她重视自己的感受,提醒她去认真回应类似于“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的生命叩问。
阿斐说从前她总觉得自己可以异于常人的超人一般的工作。甚至在做完甲状腺的手术之后,她又立刻投入到了新一份工作中,而且是一个特别繁忙的创业公司里的项目经理职位。
但当死亡拉着另一位叫做抑郁的朋友来找她时,她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超人,她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而已。
她从拒绝体验自己的感受,到开始把她觉察别人的超凡能力用到自己身上,觉察自己,再到去学习内观,做心理咨询,去感受自己的感受,学着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学会累了就停下来。
这是她有生以来离自己身体最近的时候。
阿斐还说从前她也活在主流文化里,不断地追求物质成就,而现在死亡似乎为她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不再用单一的视角去看待人生,而是学会用更多元的视角,放下自己的控制,去感受和创造真实的生命。
从从前的“进取心”到现在的“平常心”,这份向内的探求,是她回应死亡叩问的答卷。
现在的她做着一份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她说因为工作内容,工作的团队和她获得的意义感是如此美好,她甚至有些害怕有朝一日会失去这些美好。
2016年8月,她遇到了另一位被贴上“抑郁症”标签的女孩。在陪伴了她几个月后,她发现自己似乎也有些力不从心,甚至有种跟着她一起坠落的感觉。
于是她给女孩推荐了一位咨询师。其实这件事情对她来说是很难得的,因为从前很多时候她都是把全部重担一个人扛的。我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回应说:“我没有办法拯救她,我只能陪伴。”
阿斐说她也在这个过程里越来越欣赏女孩的难得,不容易和她身上闪光的部分,她说那是一种生命力的感觉。
“我不再担心因为我看到她本来的样子而不喜欢她”,阿斐这样描述。
也是在这段关系里,她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她可以跟另一个生命建立一种相互信赖,无条件地信任,尊重对方的观点也看到对方的痛苦,相互接受的,深度而稳定的连接。
女孩后来要离开北京去上海,阿斐也非常难过,但她选择让她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不是极力挽留,就像死亡教会她放下控制一样。
听到这里时我内心升起了一股暖流和力量:
看到生命本来的样子,对生命充满敬畏和尊敬,学会自我慈悲,也看到别人的不容易,欣赏一个真实的不完美的人并且跟她建立深刻的连接,做到这些的人,已经是生命的哲学家和艺术家了!
彼迈乐盐酸舍曲林片:主要用于抑郁症,亦可用于治疗强迫症。 荷氏B族维生素片:补充多种B族维生素。 顺气安神丸:调节“粘”热,镇静安神。用于“赫依”,“粘”热交争,山川间热,发烧,“赫依”引起的癫狂,昏迷,心神不安。
健客价: ¥540舒肝解郁,健脾安神。适用于轻、中度单相抑郁症属肝郁脾虚证者,症见情绪低落、兴趣下降、迟滞、入睡困难、早醒、多梦、紧张不安、急躁易怒、食少纳呆、胸闷、疲乏无力、多汗、疼痛、舌苔白或腻,脉弦或细。
健客价: ¥55适用于各种类型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广泛性焦虑症。
健客价: ¥120各种类型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广泛性焦虑症。各种类型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广泛性焦虑症。
健客价: ¥45治疗各种类型的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反应性抑郁症。治疗强迫性神经症。治疗伴有或不伴有广场恐怖的惊恐障碍。治疗社交恐怖症/社交焦虑症。
健客价: ¥96适用于各种类型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广泛性焦虑症。(详见内包装说明书)。
健客价: ¥168主要用于治疗各种类型的抑郁症和伴有抑郁症状的焦虑症以及药物依赖者戒断后的情绪障碍。
健客价: ¥66盐酸帕罗西汀片,适应症为治疗各种类型的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反应性抑郁症。常见的抑郁症状:乏力、睡眠障碍、对日常活动缺乏兴趣和愉悦感、食欲减退。 治疗强迫性神经症。常见的强迫症状:感受反复和持续的可引起明显焦虑的思想、冲动或想象、从而导致重复的行为或心理活动。 治疗伴有或不伴有广场恐怖的惊恐障碍。常见的惊恐发作症状:心悸、出汗、气短、胸痛、恶心、麻刺感和濒死感。 治疗社交恐怖症/
健客价: ¥54适用于治疗各种类型的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反应性抑郁症。治疗强迫性神经症。治疗伴有或不伴有广场恐怖的惊恐障碍。治疗社交恐怖症/社交焦虑症。其它详见说明书。
健客价: ¥55本品适用于治疗各种类型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广泛性焦虑症。
健客价: ¥102各种类型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广泛性焦虑症。
健客价: ¥21适用于各种类型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广泛性焦虑症。
健客价: ¥116用于抑郁症的治疗,对于伴有或不伴焦虑症的患者均有效。
健客价: ¥64用于治疗各种抑郁症,本品的镇静作用较强,主要用于治疗焦虑性或激动性抑郁症。
健客价: ¥241.抑郁症:百优解片用于治疗抑郁症状,伴有或不伴有焦虑症状。 2.强迫症:百优解片用于治疗伴有或不伴有抑郁的强迫观念及强迫行为。 3.神经性贪食症:百优解片用于缓解伴有或不伴有抑郁的贪食和导泻行为。
健客价: ¥258各种类型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广泛性焦虑症。
健客价: ¥58治疗各种类型的抑郁,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反应性抑郁症。常见的抑郁症状:乏力,睡眠障碍,对日常活动缺乏兴趣和愉悦感,食欲减退。治疗强迫性神经症。常见的强迫症:感受反复和持续的可引起明显焦虑的思想、冲动或想象,从而导致重复的行为或心理活动。治疗伴有或不伴有广场恐怖的惊恐障碍。常见的惊恐发作症状:心悸,出汗,气短,胸痛,恶心,麻刺感和濒死感。治疗社交恐怖症社交焦虑症常见的社交焦虑的症状:心悸,出汗,气短
健客价: ¥76用于治疗抑郁症。
健客价: ¥55治疗各种类型的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反应性抑郁症。常见的抑郁症状:乏力, 睡眠障碍,对日常活动缺乏兴趣和愉悦感,食欲减退。治疗疗效满意后,继续服用本品可防止抑郁症的复发。
健客价: ¥1521、舍曲林用于治疗抑郁症的相关症状,包括伴随焦虑、有或无躁狂史的抑郁症。疗效满意后,继续服用舍曲林可有效地防止抑郁症的复发和再发。 2、舍曲林也用于治疗强迫症。疗效满意后,继续服用舍曲林可有效地防止强迫症初始症状的复发。
健客价: ¥80适应症为治疗各种类型的抑郁症、强迫性神经症、伴有或不伴有广场恐怖症的惊恐障碍、社交恐怖症/社交焦虑症。(详见内包装说明书)
健客价: ¥75盐酸帕罗西汀片,适应症为治疗各种类型的抑郁症,包括伴有焦虑的抑郁症及反应性抑郁症。常见的抑郁症状:乏力、睡眠障碍、对日常活动缺乏兴趣和愉悦感、食欲减退。治疗强迫性神经症。常见的强迫症状:感受反复和持续的可引起明显焦虑的思想、冲动或想象、从而导致重复的行为或心理活动。治疗伴有或不伴有广场恐怖的惊恐障碍。常见的惊恐发作症状:心悸、出汗、气短、胸痛、恶心、麻刺感和濒死感。治疗社交恐怖症/社交焦虑症。常见
健客价: ¥55用于治疗各种抑郁症,本品的镇静作用较强,主要用于治疗焦虑性或激动性抑郁症。
健客价: ¥21用于抑郁症的治疗。
健客价: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