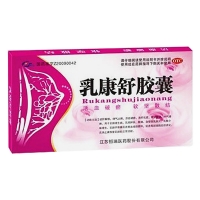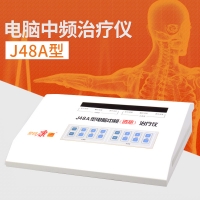很多人说,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恋人,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我父母总觉得不够好,怎样才能让他们接纳真实的我?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这么问:为什么非要让父母接纳真实的你?这背后的诉求究竟是什么?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被讨厌的勇气》。它是两位日本作者岸见一郎和古贺史健对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理论的解读,因为文化相似,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东亚文化强调集体主义,鼓励我们多为别人着想,但《被讨厌的勇气》里指出,过度在意别人的感受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比如前面提到的例子,问题不在于“父母不接纳真实的你”,而在于,你为何那么在意父母的对你的看法?
让你烦恼的不是父母,而是你自己
先介绍一下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他最初是弗洛伊德的同事,后来他反对精神分析学说,创办了个体心理学,这就是《被讨厌的勇气》一书的理论依据。
阿德勒认为,情绪是有目的的。如果我们自己将自己生活中的痛苦都归因为父母的问题,将自己困在“因为父母不好”,“因为父母不认可我”之中,那么我们这些情绪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父母发生改变。
这恰好是我们一直在抱怨的事情:父母总是想要改变我,并把自己生活中的不幸归因在我的身上,比如非要我有份稳定的工作、在多少岁之前结婚,就好像他们生活中的失望和痛苦都是我造成的。
我们觉得父母这样归因是错的,让我们觉得窒息;但是,当我们试图改变父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对父母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如果父母能够听我的,我的人生就幸福了。
你可以坚持做自己,父母也可以不高兴
在前面提到的这种互动中,实际上双方都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和情绪承担责任。
阿德勒认为谁也没必要去满足别人的期待,并提出了“课题分离”的主张,简单来说,就是分清楚一件事到底是谁的责任。
举个例子:
假设一对父母不喜欢女儿的男朋友,觉得女儿和他在一起不会幸福。但是,选择和谁结婚是女儿的课题,不是父母的课题;这段婚姻带来的任何后果,不管是好是坏,也只能由女儿一个人承担。所以,父母如果觉得女儿的男朋友不靠谱,他们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们不能强迫女儿分手。
课题分离的方法适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但是在关系亲密的人之间,课题分离会更加困难。许多父母会把孩子看作自己的一部分,把孩子的课题当成自己的课题。他们可能会说:“看见你这样,我不能不管你。”但是实际上,每一次他们的干涉起效了,他们就会更加相信“孩子需要我”。
而对于子女来说,如果觉得“因为有糟糕的父母,我才这么不快乐”,这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情绪当成了父母的课题,希望父母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按照前面提到的目的论,这种想法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现状很不满意,所以我要责怪我的父母”。
课题分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既不要干涉别人的课题,也不要让别人干涉自己的课题。放在亲子关系中,就是:不要干涉父母的情绪,也不要让他们干涉你的人生。
要想不让别人干涉自己的人生,那就只能主动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你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那是你自己的课题;但是,父母如何评价你的选择,如何克服这种“孩子不听话怎么办”的痛苦,这是他们的课题。
渴望被肯定的孩子,其实还没有真正长大
你是否有这个能力,允许父母对你不满和失望?
这个问题背后真正的议题是:一个人是否完成了“分离个体化”,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从心理上是否真正成年、和父母分离、独立了起来。
很多时候,我们妥协的原因是无法忍受父母对自己表达不满、失望,就好像当他们对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值得被爱、被尊重的孩子了,感觉自己特别糟糕。因此,无论父母的要求或者期待是否合理,我们内心都涌起巨大的内疚感,推动着我们去牺牲自己,满足父母的期望。
这种牺牲表面上看是我们忍让包容了父母,但与此同时,我们其实有了一个巨大的借口:就是当初都是你要我这么做的,看我的人生多么不如意,都是父母的错。
所以,分离个体化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发展出允许他人对我们失望、生气的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将这个责任推到父母或者他人身上。
建立“横向关系”,找到被需要的感觉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课题分离就是为所欲为,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吗?
不是的。
被人讨厌是自由的代价,但你还可以在其他地方寻找自己的价值。
太在意他人的感受和评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关心别人,实际上这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也就是把自己看得过于重要,觉得其他人都应该喜欢自己、肯定自己。
但是,表扬和肯定也可能意味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比如孩子动手做了一件礼物送给妈妈,妈妈说“你真棒”,这里面就隐含了一种强者对弱者的评价。
阿德勒将这种关系称为“纵向关系”,他认为我们应该避免纵向关系,建立一种更加平等的“横向关系”。在横向关系里,我们会更多地表达鼓励和感谢,比如在前面的例子里,如果妈妈回答说“我很高兴,谢谢你”,这就是一种不带评价色彩、饱含尊重的关系,孩子就能感觉到自己做的事是有价值的,自己的存在也是有价值的。
阿德勒建议我们跳出令自己感到困扰的关系,和更多的人建立平等的横向关系。通过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我们就能够更多地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从不一样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位置。比如,你在父母眼里也许是个糟糕的孩子,但是你可以是一个受欢迎的朋友,一个优秀的职场人;也可能你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是伴侣和孩子依恋的人。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不取决于他人的评价,它只取决于你自己做了什么,以及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
总之,只要你能在其他地方找到自己的位置,经常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是被人需要的,那么少数人的不满意对你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愿你也能勇敢地,做个“被讨厌的人”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现在的不幸是过去的创伤造成的,但阿德勒强调个体的力量,他认为真正决定我们的不是经历,是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
关系越亲密,我们就越在意对方对我们的看法,得不到父母的认可的确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但是,与父母缠斗已久的你想必已经知道,就算委屈自己去迎合他们,你同样会觉得很不甘心。
所以,不为他人的情绪所绑架,哪怕感到痛苦也要迈向自己的人生,去拥抱大千世界的更多可能,这才是成长呀。
希望你也能找到“被讨厌的勇气”。
在童年时期,我们对自身和外界的理解都非常有限,因此我们不知道怎样去评价自己,只能求助于父母。如果父母肯定了我们,我们便能肯定自己,渐渐生长出自信;而如果父母总是批评我们,我们就会不断批评自己,改造自己,直到开始怀疑自己。
得到父母认可的愿望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始终跟随着我们。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隆写过一部短篇小说,叫《妈妈及生命的意义》。小说主人公已经垂垂老矣,他在濒死的幻象中回到了童年,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游乐园里,朝妈妈挥着双手,大喊:
“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
source:LadyBird
我们当然希望父母能理解、支持我们的每一个决定,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等待那个认可,我们就会被困在父母的世界里,由他们的观念和喜好决定自己的行动。
其实啊,我们再也无法知道过去父母否定、拒绝我们的每一个真正的原因,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主动认可自己。
这里说的“认可”有很多种意义:
当你染了亮色的头发,被妈妈啧啧嫌弃的时候,你可以扬着头说:“可是我觉得好看!”
当你升职加薪,爸爸却提醒你不可骄傲的时候,你可以得意地说:“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当你想要辞职、旅行、和心爱的人结婚,而父母不同意的时候,你可以说:“我的事情我自己决定。”
source:MartinKundby
主动认可自己并不容易,我们需要回到过去,找回当年被磨损的自信。我们要找到当年那个委屈的自己,告诉自己:没关系的,别管爸爸妈妈说什么,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们还要学会坦然面对父母的不解、愤怒和失望。我们可以责备父母的苛刻,可以抱怨他们的不理解,但不要让他们的情绪困住我们的脚步。
有人可能会说:“但是,看到妈妈那个样子,我也很难过,我好想变得狠心一点啊。”
不,你不用做一个“狠心”的人。你只需要找到自己的边界,进而疗愈与父母的关系。
如果我们能够在回忆中探索自己的成长经历,理解自己家庭中的故事,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今天的样子,从而意识到:我的每一种感受、每一个愿望都是独特的,都有它存在的充分理由,没有人可以把它夺走。
当你确认了自己的边界,找到了自己的力量,你便能坦然面对父母的情绪了。
这个过程也许会很漫长,但是此刻就能开始。
本品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躁狂发作。
健客价: ¥219富马酸喹硫平片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躁狂发作。
健客价: ¥90.5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消散乳块。用于肝气郁结,气滞血瘀,乳腺增生,乳房胀痛。
健客价: ¥24疏肝解郁,理气止痛,活血破瘀,消积化痰,软坚散结,补气健脾。用于乳腺增生病。
健客价: ¥10.8疏肝解郁,理气止痛,活血破瘀,消积化痰,软坚散结,补气健脾。用于乳腺增生病。
健客价: ¥29疏肝解郁,理气止痛,活血破瘀,消积化痰,软坚散结,补气健脾。用于乳腺增生病。
健客价: ¥17疏肝解郁,理气止痛,活血破瘀,消积化痰,软坚散结,补气健脾。用于乳腺增生病。
健客价: ¥35祛心“赫依”病。用于心烦失眠,心神不安,对心“赫依”病尤为有效。
健客价: ¥32缓解成人便秘的症状。
健客价: ¥16温中散寒,补脾止泻。用于大便失调,黎明泻泄,肠泻腹痛,不思饮食,面黄体瘦,腰酸腿软。
健客价: ¥25.5该产品用于体外监测人体毛细血管全血中的葡萄糖浓度。
健客价: ¥654彝 医:补知凯扎诺,且凯色土。 中 医:益肾,活血,软坚散结。主用于肾阳不足、气滞血瘀所致的乳腺增生。
健客价: ¥51.68彝医:补知凯扎诺,且凯色土。 中医:益肾。活血,软坚散结。用于肾阳不足、气滞血瘀所致的乳腺增生。
健客价: ¥37.9活血化瘀。用于血瘀型胸痹及血瘀型轻度脑动脉硬化引起的眩晕,冠心病,心绞痛。
健客价: ¥37.8温肾疏肝,行气活血,调理冲任,止痛散结。主治肾虚肝郁,气滞血淤,肾虚肝郁、冲任失调型乳腺增生病、高泌乳血症、月经失调等。
健客价: ¥7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或遵医嘱。
健客价: ¥628当单用饮食疗法、运动治疗和减轻体重不足以控制血糖水平的成人2型糖尿病。
健客价: ¥9用于过敏性皮炎、亚急性慢性湿疹、阴囊湿疹、皮肤瘙痒症和外阴瘙痒等。
健客价: ¥4.5用于治疗手癣、足癣、体癣、股癣、花斑癣及皮肤念珠菌病等。
健客价: ¥91、情绪易紧张、暴燥者及失眠人士;2、牙齿状况不佳、患有骨质疏松、经常腰背酸痛和痛经者;3、经常饮用碳酸饮料者;4、公司白领、上夜班者;5、素食者、婴幼儿和老年人。
健客价: ¥98镇痛、各部位软组织损伤、颈椎病;消炎、消肿、盆腔炎、附件炎、注射后硬结、肠梗阻;胃下垂、胃肠功能紊乱; 瘢痕疙瘩、术后粘连、慢性炎症等。
健客价: ¥1669原装全日康中频治疗仪J18B型号专用吸适电极,治疗仪附件,需配合主机使用。
健客价: ¥29全日康J18B型电脑中频治疗仪,利用中频脉冲电刺激理论,最新研制而成的家庭型治疗仪,其综合了国内多位专家,教授多年临床经验,是在J18A型治疗仪基础上,为了满足广大用户的要求研制的新机型。
健客价: ¥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