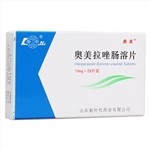最近,一场由李安导演执导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引起了众多朋友们对战争、军人待遇的热议。往往在提到战争这个关键词,就可以联想到其代表着对人类文明“毁灭”与“重塑”的双重作用。
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前所未有的大灾难进行的统计显示,在四年内死了超过800万的男性。在这场人为的浩劫过后,欧洲有四个帝国灭亡,许多西方文明赖以维系的重要信念也随之动摇。
经过这场战争的蹂躏过后,连续暴露在战场壕沟之中,处于极端恐惧的状态之下,使得面临精神崩溃的军人数目大增。受困的绝望、不停地遭受来自死亡的威胁、还要被迫目睹战友的残废与死亡而没有任何可以救助的指望。这一切使这些军人仿佛回到了“恐怖蜡像馆”一般的癔症时代,并奇怪地罹患了类似歇斯底里的神经症:他们开始失控地尖叫和哭泣,行动僵硬且无法移动、变得沉默和没有反应,好似也失去了记忆与感觉的能力。产生这类精神症状的军人数量如此庞大,以至于需要大量的医院来容纳他们。这无疑迫使英国国内增加了医学界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并迫切地将研究此类精神崩溃的症状的器质性因素提上议程,并把这种精神崩溃的症状称为战争所致的创伤性神经症(即战争性神经症)。而在2016年的今天,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它以一个重新被世人皆知的新名字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PTSD)。
现代精神医学与心理学界不仅将创伤后应激障碍单纯用于对战争的研究和理论解释范围,更多地将其应用于由于重大创伤事件引起的心-身问题。就好像哈特曼创建了自我心理学使精神分析学从病理的角度扩展到正常的角度一样,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名词现今充满了更多日常生活中的“创伤”问题,即:(1)挫折;(2)冲突与(3)压力。
现在对于“创伤”的研究已经成为了一条线段,按照严重等级来划分,“最轻微的一端可以由生活中相对的极小的创伤事件造成,最严重的一端则相对性地具有特别的压力性,因为此应激源的强度极大,通常个体的应对风格和技能都没能起到作用”。比如:冲突剧烈的离婚、惨烈的自然灾害以及受伤或生病之后,出于心理内部系统或者外部因素的要求,都会使个体对自我概念和生活方式进行困难的再适应,从而导致危机或创伤。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只有负面心理事件才会给个体带来应激性”。如果在赢得了渴望的升迁或者准备结婚这样的积极变化,都会对我们自身产生新的要求,从而赋予应激性。所以我们遵循对于应激方面的规则是:“改变越快,应激强度也就越大(二者存在正相关性)”。
尽管通常出乎意料新的调适需要出现,且我们没有现成的应对策略可用时,都会将个体置于严重的应激之下,但个体也同样存在对应激源的知觉同个体的应激耐受性的心理策略。
对前者而言,个体可以掌握对心理社会环境中可能有害的应激状况的了解,就是我们俗称的“心理准备”。理解应激情境的性质,为此做好准备,并知道它会持续多长时间,这都会减轻应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而对后者来说,不能应对不断改变的生活环境的个体,对最轻微的挫折或压力都会特别敏感。与那些总体上感觉自信与安全的个体相比,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足够价值和能力的个体更有可能会体验到威胁。应激耐受性这一术语主要是指耐受应激而不会受到严重损害的能力。当然,这会与一定的人格特质具有相关性:“有些人看上去天生比别人‘脆弱’,对最轻微的改变也难以应对,其身体耐力不是很好,面对应激或应激情境时容易疲劳和生病”。在应激应对的总体能力上,个体的学习经历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虽然应激障碍的人格研究表明了一些个体存在的易感性确实在面对应激创伤方面表现颇高,但这并不能作为严格衡量个体应激发展(由急性应激状态到慢性应激状态)的重要指标。事实上,即便有些个体会表现出应激层面较为严重的适应困难,但大量的证据表明:“积极的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可以调节应激作用于人的效应,甚至可以减少疾病与早期死亡所造成的风险(Monroe&Stener,1986)”。与之相反,个体在应激状态下越是缺乏外在支持,无论是人际支持还是物质支持,都会使一个给定的应激源所造成的危机或是创伤加强,从而进一步削弱个体的应对能力。所以,古语“家和万事兴”这句话在应激状态下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就好像那句:“人际关系可以治病,也同样可以致病”。综上,当生活并未按照我们所想的那般行进时,个体(在应激状态下)被迫使去做出何种心理决策,与是否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都将成为后期健康适应的重要指标。
So,whataboutthe“Stockholmsyndrome”?
在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做出相应的创伤心理问题研究时,在百度上键入“stockholmsydrome(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为关键词,就会看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那句著名台词:“人,是可以被驯养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影视题材(例如《他来了,请闭眼》等)介绍刑事犯罪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现象,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逐渐被大众广泛认知。但创伤心理研究对斯德哥尔摩效应的解释还缺乏准确的临床描述。基于此现状并结合精神分析视角进行研究之后,我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解释归根于一种“心理退行”的机制。并尝试运用MargaretS·Mahler的“分离-个体化”理论的“和解期”为主来阐释。
一直以来,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令人着迷却又困惑不解的地方就在于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的亲犯罪者行为。在历史的调查研究中,精神医学专家们就开始对集中营的战俘、囚犯、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进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方面的统计,统计结果表明,在这些个体中,大多数都存在了或多或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体验,即“最终会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
在这样的行为背后,事实上病人是一种退行到了Mahler所提出“和解期”的心理层面的体验。犯罪者更多地打破了病人曾经所拥有的“客体永久性”(即认为能给予爱的能量的主要个体始终存在的一种心理体验),将其通过暴力手段重置到病人儿童时期的心理状态。于是,在这个基础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发生的契机出现了,病人的双重自我状态也随之诞生了。这种极为矛盾的双重自我状态的出现(对于双重自我概念,并非是指诸如DID的解离性心理障碍,而是一种为了保持真实自我不致于遭到毁灭的第二个颇具适应创伤情境的自我状态),正是在长期处于慢性、高强度的(可威胁到生命的)应激状态下的一种新的保护系统的建立。
正如描述所显示的那般:“并不是所有的受虐个体都可以迅速掌握一种具有适应性和保护性的能力,而即使掌握了这种保护性的适应能力,个体也不可能在长期应激下始终有效地应用它”。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创伤性的心理状态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派生的最主要目的是:保护。
所以,深谙“分离—个体化”时期的精神分析同仁与临床学家、教育心理学家在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个体出现的行为症状学观察结果上不难发现,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病人个体,都极为类似地表现出了Mahler提出的儿童和解亚阶段的“shadowingpattern(尾随模式)”同“dartingpattern(离弃模式)。”一方面,尾随模式代表着儿童想要回归到爱的(或可依赖的)客体身边的愿望,放到斯德哥尔摩问题上来讲,则是暴力手段如此可怕,已经切断了和曾经爱的客体的联系,加之自身所处的环境类似于待宰的羔羊一般,犯罪者的身份逐渐作为新的、畸形的爱的客体出现。而另一方面,离弃模式是代表儿童害怕再回到与母亲融合的状态而不能独立的一种焦虑情绪,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病人,更多地是想在尾随模式的被动建立情况下,保证自我不受到来自犯罪者的彻底侵蚀(离弃模式)。
综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患者,其实是又一次经历了早年的、带有病理性质的分离-个体化时期。对于心理治疗师来说,如何陪伴,如何促进他们的成长,帮助他们体验到安全,是极早帮助他们摆脱慢性应激的良策。
乳果糖口服溶液: - 慢性或习惯性便秘:调节结肠的生理节律。 - 肝性脑病(PSE):用于治疗和预防肝昏迷或昏迷前状态。 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溶胶囊:治疗肠道菌群失调(抗生素、化疗药物等)引起的腹泻、便秘、肠炎、腹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等。
健客价: ¥756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返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29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5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氏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22适用于Tourette综合征(发声与多种运动联合抽动障碍)。
健客价: ¥138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 (胃泌素瘤)。
健客价: ¥10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18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33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10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11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10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9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22主要用于脑部、周边等血液循环障碍。 1、急慢性脑机能不全及其后遗症:中风、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衰退、痴呆。 2、耳部血流及神经障碍:耳鸣、眩晕、听力减退、耳迷路综合征。 3、眼部血流及神经障碍: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及神经障碍、老年黄斑变性、视力模糊、慢性青光眼。 4、末梢循环障碍:各种动脉闭塞症、间歇性跛行症、手脚麻痹冰冷、四肢酸痛。
健客价: ¥351.治疗Sj?gren综合征(口、眼、鼻干燥综合症)的干燥症状,纠正因服用某些药品(如安定剂、 抗抑郁药、抗帕金森病药等)引起的药源性及U咽区接受放射治疗后引起的口干症。2.用于胆囊炎、胆结石, 并用于伴有胆汁分泌障碍的慢性肝炎辅助治疗。
健客价: ¥15.9用于以下患者的预防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事件: ·心肌梗死患者(从几天到小于35天),缺血性卒中患者(从7天到小于6个月)或确诊外周动脉性疾病的患者。 ·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患者 -非ST段抬高性急性冠脉综合征(包括不稳定性心绞痛或非Q波心肌梗死),包括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后置入支架的患者,与阿司匹林合用。 -用于ST段抬高性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与阿司匹林联用,可合并在溶栓治疗中使用。
健客价: ¥65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3.5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18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9.9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11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12.2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5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10适用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应激性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和卓-艾综合征(胃泌素瘤)。
健客价: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