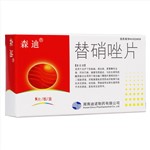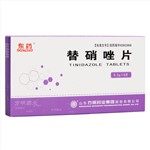先天性马蹄内翻足是肌肉骨骼系统常见的先天性疾患之一,畸形始于胚胎期,生后即可发现,表现典型,容易确立诊断。但是,对于该病的治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甚至贯穿了整个骨科发展史,至今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方案。为此,特就本病的治疗做系统回顾,以指导未来的工作。
一、历史回顾
关于马蹄内翻足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公元前400年Hippocrates的描述,他认为致病因素为机械压迫,发现大多数病例能够通过连续
按摩获得矫正,应在骨性畸形形成之前尽早开始治疗,为防止复发需要过度矫正并维持。Hippocrates的方法是生后尽早开始反复手法按摩,然后采用强力绷带维持矫正位,虽然没有技术细节的描述,但强调了轻柔操作的重要性,治疗结束后穿用特制鞋以维持矫正并防止复发。遗憾的是这些技术后来被遗忘。
1658年,Arcaeus描述反复牵拉治疗,他采用两个机械装置来维持矫正。18世纪中叶,Cheselden采用反复牵拉、胶带维持矫正位。1803年,Scarpa发表了《儿童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的历史回顾》,认为距骨的位置和形态是正常的,畸形是前足相对于距骨头向内侧脱位所致,治疗采用强力手法而非轻柔牵拉,然后使用复杂的机械装置进行维持,后人称之为Scarpa‘s鞋。Scarpa方法由于其他人均不能成功使用,而未被广泛接受。1806年,TimothysSheldrake发表了笔谈《儿童腿足扭曲畸形》,称多数病例2~3个月能够得到矫正,但是行走期之前不能放任不管。认为致病因素一半是韧带,另一半是肌肉。发现生后2个月内开始治疗者在行走期有望获得矫正,开始治疗年龄越大需要的疗程越长。1823年,Delpech对两例获得性马蹄内翻足实施了经皮跟腱切断术,均并发了感染。1831年,Stromeyer进行了几例经皮跟腱切断的实践,没有发生感染。英国年轻医生W.J.Little因为
脊髓灰质炎患有马蹄内翻足畸形,Stromeyer对其进行经皮跟腱切断获得成功。随后,Little将该手术引入英国并获得巨大成功。Little对机械压迫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宫内
发育阶段异常的肌肉挛缩是导致畸形的原因,除足部畸形外,该病累及整个下肢,由此衍生出足到骨盆的固定装置。
1838年,M,Guerin首次采用Paris石膏来治疗先天性马蹄内翻足。1934年,DenisBrowne(英国小儿外科之父)推荐初始强力矫正后使用支具维持,类似支具仍在使用。
1866年,Adams第一个意识到将经皮跟腱切断作为马蹄内翻足的第一步治疗是错误的。通过胎儿畸形足标本的解剖发现并不存在骨结构性异常。Adams认为肌力异常为致畸因素,马蹄内翻足的解剖学表现为距跟舟关节脱位,只有舟骨和跟骨获得复位,距骨才可能恢复正常的形态和位置,推荐早期手术来实现解剖复位,同意Scarpa先矫正内翻后矫正跖屈的理念,设计了腿外侧直夹板用来维持矫正。伴随着无菌技术和麻醉概念的确立,马蹄内翻足的手术治疗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1891年,Phelps采用跟腱切断+内侧松解,延长胫后肌,松解踝关节内侧韧带、跖筋膜、踇展肌、屈踇长肌、所有短屈肌,最后进行距骨颈截骨和跟骨楔形截骨。Duval(1890年),Ogston(1902年)和Lane(1893年)均实施了类似的“根治性”手术。19世纪晚期,针对距骨的矫正手术开始流行。Lund(1872年)、Agustoni(1888年)、Morestin(1901年)采用距骨切除术来改善足部的位置。
1908年,RobertJones实施了跗骨截骨和楔形切除术,术前需要通过手法按摩和石膏固定获得尽可能多的矫正,术中尽可能少的切除骨块。但是骨性手术的指征并不明确。1920年,Elmslie认为上述手术过于激进,妨碍畸形矫正的因素主要来自于距舟关节囊、跖筋膜、跟腱,而胫后肌腱的作用较弱。Ober(1920年)持类似观点。1930年,Brockman采取松解内侧韧带和跖筋膜,切断踇展肌、胫后肌,最后延长跟腱纠正跖屈畸形。因畸形足术后僵硬最终放弃了该术式,认为广泛的软组织松解将形成广泛的纤维组织瘢痕。Steindler报告该术式仅45%结果良好。Elmslie,Ober和Brockman均强调了矫正完成之前石膏固定的重要性,在进行跖屈矫正之前其它畸形必须首先获得矫正。Dunn(1922年)首次描述了胫前肌腱移位用以防止畸形复发。GarceaulManning(1947年)报告86例复发畸形采用胫前肌腱移位治疗,83%结果良好。Barr(1958年)认为如果腓骨长肌有功能的话,不能进行胫前肌腱外移,否则将继发肌力不平衡。所有主张手术治疗者均认为重度病例即使采用长期手法按摩和石膏治疗,结果仍令人失望;而早期顺列骨性关系有望获得正常的解剖结构。但手术时机、手术范围及结果评定并未达成共识,同时缺乏长期随访。认识的缺陷必然导致原始畸形矫正不良,同时出现严重的医源性问题。手术不可避免地继发深部瘢痕,在婴幼儿病例中更为严重。手术的平均失败率为25%(13%~50%),存在诸多并发症,包括切口愈合问题,神经血管损伤,骨/软骨损伤,距骨和舟骨缺血坏死,疼痛,僵硬,无力,畸形残留/复发,过度矫正等。
在20世纪早中期,Kite成为保守治疗的领导者。他沿用了Hoke采用手法按摩、石膏固定维持矫正位的治疗理念,分别矫正畸形成分而不是同时矫正。通过在中跗关节外展前足进行矫正,拇指按压在足外侧跟骰关节处作为对抗支点,这样跟骨的外展将受到限制,因此妨碍了足跟内翻的矫正。能够矫正高弓避免足部旋前,但需要数月时间、多次更换石膏来缓慢矫正足跟内翻以获得跖行足。由于疗程过长,失去了许多追随者。
许多医生采用Kite方法并未获得成功,于是在1960—1990年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手术治疗方法。DillwynEvans(1961年)描述了软组织松解+跟骰关节融合的联合手术。LeonardGoldner(1969年)认为主要畸形是距骨在踝穴中内旋,采用四象限松解(包括三角韧带松解术)。NorrisC.Carroll(1978年)研究了胎儿马蹄内翻足标本,发现距骨体长轴外旋,术中应矫正所有畸形成分,包括跖侧松解、Henry’s结松解、Z字形延长跟腱和胫后肌、后侧关节囊松解、距舟关节切开复位、纠正前足内收和旋后、克氏针固定中跗关节以及中立位修复肌腱。VincentJ.Turco(1979年)采用内侧切口行一期后内侧松解,认为该术式能够充分矫正畸形,术中充分矫正和临时内固定是
持久维持的关键,应力背屈侧位X线片能够准确、可靠地评价畸形矫正效果。GeorgeSimons(1980年)采用距下关节环周松解和距跟骨间韧带松解。DouglasMcKay(1982年)采用广泛的内、后、外侧松解以纠正跟骨的水平旋转、外移和跖屈。Carroll和McKay均强调了保留距跟骨间韧带的重要性,否则有跟骨外移的风险,出现灾难性并发症。Dobbs报告了手术治疗45例平均31年随访情况,仅27%结果优良,X线显示近50%的病例距舟关节、跟骰关节和距下关节出现中重度骨性
关节炎。此后相继有远期结果差的报道,至此一期广泛松解手术开始降温。
在20世纪中后期,Ponseti通过对马蹄内翻足病理生理学的研究以及总结前人的失误提出了他的治疗方法。对Ponseti产生深远影响的学说其实早已存在:Farabeuf(1872年)描述了正常足当跟骨在距骨下方旋转时如何发生内收、屈曲和内翻,更准确地说,当足部内翻时,跟骨在距下内收和内翻,同时骰骨和舟骨分别在跟骨和距骨头前方内收和内翻。Huson(1961年)证实跗骨关节不是单一铰链的活动,而是围绕一个动轴进行旋转,而且跗骨关节同时发生运动,如果一个关节的活动受阻,其它关节功能也将受到限制。在此基础上,Ponseti提出了他的治疗指南:①除了最后矫正跖屈畸形以外,马蹄内翻足的所有畸形成分必须同时矫正。②前足相对于后足旋前导致的高弓畸形,通过旋后前足与中足顺列获得矫正。③当全足处于旋后和屈曲位时,就能够在距骨下轻柔地逐渐外展。通过拇指按压距骨头外侧作为对抗,就避免了踝穴中的旋转。④当全足充分外展获得在距骨下最大外旋时,足跟内翻和足部旋后将获得矫正,绝不能将足外翻。⑤距下畸形矫正后,逐渐将全足背屈来纠正踝关节跖屈畸形,常需行经皮跟腱切断来易化治疗。Ponseti技术首次发表于1963年,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0年远期结果报道以后才开始赢得广泛关注。
1970年,Masse和Bensahel研发了法国功能性治疗法,之后得到Dimeglio和Richards的推广,是一种动态治疗方法,包括每日由专业理疗师进行手法按摩,然后采用弹性/非弹性绷带固定维持。首先矫正水平面畸形,最后矫正跖屈畸形。也可使用CPM(continuouspassivemotion,持续被动活动)设备每日连续矫正16~18h,最后通过小腿三头肌腱膜切断矫正残留的跖屈畸形。每3~6个月拍片检查。Diméglio发现重度畸形(评分11~15)中12.6%需要后侧/后内侧松解、极重畸形(评分16~20)中70%需要后侧/后内侧松解。该方法技术要求严苛,可成功治疗中、重度畸形,极重畸形的失败率很高。由于需要专业技术人员长时间治疗、且费用较高,因而未得到普及。
二、现状
目前,对于马蹄内翻足骨科医生们在病理解剖学、病因和畸形严重程度分类以及早期治疗上已达成共识。而对于复发畸形和大龄病例的治疗,由于年龄和畸形程度差异较大,尚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的主要畸形包括后足内翻(距下关节)和跖屈(踝关节)、前足内收(相对于中足)和高弓(前足相对于后足跖屈),是骨形态异常和骨间关系异常的结果。
需要进行全面的肌肉骨骼系统检查,进行病因学分类:①姿势性—畸形轻,通过手法按摩加石膏矫正,能够完全恢复。②特发性—不同严重程度的单纯足部畸形。③神经性—合并神经肌肉疾患,如脊髓脊膜膨出等。④综合征性—合并其它畸形,足部畸形常很僵硬。
Pirani评分和Dimélio分级是迄今为止两种可信度较高的畸形严重程度的分类方法。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的治疗目的是获得跖行、柔软、无痛和功能良好的足,无需支具或矫正鞋辅助行走。
相关文献绝大多数为回顾性研究,综合结果显示非手术治疗可望获得优良的远期结果,而广泛松解治疗在青少年期可有良好的短期结果,但是到了成人期将变成疼痛和僵硬的足,即远期疗效并不令人满意!
目前Ponseti技术成为早期保守治疗的首选方法,被接受程度和普及率最高。只有当前足相对于踝关节平面很容易外展到60°以上,方可进行跖屈畸形的矫正。多数病例跖屈畸形很难通过石膏完成矫正,80%~95%需行经皮跟腱切断术。畸形充分矫正后,全天佩戴外展支具3个月,然后夜间和睡眠时使用到2~4岁。初始矫正的成功率95%左右,复发率37%~47%。支具维持的顺应性差与畸形复发率高度相关。对于动力性旋后足,胫前肌腱外移至外侧楔骨可以防止复发。Laaveg和Ponseti建议畸形复发后采用手术治疗,可选择的术式有跟腱延长、后侧松解、跖筋膜松解,通常不需要广泛的后内外侧松解。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由于早期保守治疗在临床的广泛运用,传统手术治疗的比例已逐年下降。
保守治疗无效的顽固畸形或复发畸形,有手术治疗的指证。绝大多数复发实际上是第一次矫正不充分的延续。如果初始治疗矫正充分,则复发与神经源性不平衡有关。反复手术和制动必然会加重足部僵硬和无力,因此,翻修术应采用尽可能少的操作最终实现可靠的跖行足负重。由于病情的绝对个性化特征,目前尚无标准方法可循。因此,术前需要做好完整的评估和计划,比如手术时机(9~12个月接近负重行走期为宜)、手术范围、手术方法、术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随生长可能出现的变化及挽救办法等等。第一次手术是获得持久矫正的最佳时机。年幼病例首先采用Ponseti技术进行矫正,不能纠正的畸形采用针对性手术处理。大龄病例则需要附加截骨术,如外侧柱短缩截骨术纠正前足内收,中足截骨纠正高弓和内翻,跟骨截骨纠正后足内翻。
不同学者报道了多个手术切口,而更为重要的是切口之下所进行的操作,只有能够安全有效地显露和治疗所有畸形元素者才是最合理的选择。常用的手术入路有Turco后内侧切口、Cincinnati环距下关节切口、Carroll双切口。
多次术后复发、严重僵硬的畸形,治疗的重点是解决疼痛和功能问题。治疗方法有软组织松解+截骨术,关节融合术,外固定架逐渐矫正术。三关节融合术将缩短足的纵径,同时应力向踝关节转移导致退行性关节病,已有多篇文献在长期随诊总结基础上提出否定此术式的结论。Grill和Franke推广了Ilizarov技术在足部畸形矫正中的应用,此后许多学者将其用于严重复发畸形、软组织条件差或大龄病例的矫正,取得了初步满意的疗效,但是仍缺乏长期随诊结果的分析评价。
我国现阶段临床病例可分为四类:未治病例,保守治疗失败病例,手术后复发或残留畸形,大龄病例。需要根据病人年龄和畸形严重程度选择治疗方法。距下畸形(高弓、内收、内翻)可以首先采用Ponseti技术进行矫正,无效或残留畸形再考虑手术治疗。距上畸形(跖屈)最难矫正,多需要手术治疗,如果踝关节跖屈≤30°,经皮腱切(≤1岁)或后侧松解(>1岁)即可奏效,而踝关节固定跖屈>30°,特别是合并骨性畸形或软组织条件差者,采用外固定架逐渐矫正更为安全有效。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的治疗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医生、患者特别是家属三方积极沟通和配合,术后需要加强主、被动功能训练,有效维持,密切随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免复发和加重。
三、未来
Ponseti认为马蹄内翻足的治疗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一个柔软有功能的足即使残留轻微畸形,也要好于那些虽然矫正充分但是僵硬、疼痛的足。
通过健康宣教和技术培训,普及早期保守治疗。为了获得无痛、功能良好、外观正常的足,需要进一步研究来充分理解发病机制和治疗的影响,包括矫正效果、长期结果和生活质量。对于Ponseti技术需要参透细节规范应用。非手术治疗应作为起始治疗手段,一个完整的治疗计划应包括手法按摩+石膏矫正、经皮跟腱切断、支具维持、肌力平衡以及残留/复发畸形的处理,并应进行长期的随访观察。
改进畸形严重程度的分类方法,使结果评估更为准确和便于比较。通过循证医学和长期随访比较来寻找最佳治疗方法,同时寻求更好的维持方法,提高支具的顺应性。更好地了解发病机制,已经发现许多调控基因可以引起轴下肌群早期肌细胞生成的多样性,由此可进一步探索基因治疗来预防畸形。
总之,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的治疗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之路,从原始保守治疗转向手术治疗又重新回归到现代保守治疗,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未达到理想的境界。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小儿骨科同仁不断地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提高认识,少走弯路,寻求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提升疗效,更好地造福于患者。